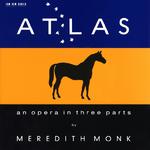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第四百三十一集 这一切只有在如此的天气才会得见 别有一番美意 溪水踱步在青石板的湖岸边 被眼前的一幕幕烟波美景深深吸引 甚至有吟诗一首的冲动 直到看见不远处伸出湖面有一处码头 小巧而精致 堪堪只能停泊一条细长的画船 这会儿船家似乎躲雨不见身影 而在船舱内却有一位小姐家好似在焦急的等待 溪水不由得快走几步 待上了码头往船上递送目光时 恰好那位小姐也回过头来 那眉眼如茭白月光 盛满盈盈秋水 那鼻翼如远山秋意 微微挺立 那唇如降珠红果 轻轻一点 视为天人也一点也不为过 小姐见一位书生不知何时而来 一直盯着 忙先别过头去 习水也觉有些唐突 只是这一眼已然万年 好像是前世所见 今生重逢一般 叔在家冒昧打扰 不知小姐为何雨中至此 眼见雨翼更甚 划船内遮挡不足 但雨大时会打湿衣襟 那如画中般的美人做了个万福回道 多谢公子 只因下人久久未归 也只好暂在船上避雨 溪水几乎下意识马上说道 在下有把竹伞 正好也用不上 不如小姐先拿去用吧 此刻雨又大了几分 见公子半径湿润 还是公子用吧 啊 不妨不妨 在下早已习惯了江南的烟雨 若是遮雨早就撑开了伞 这雨下得越发大了起来 湖水上涨 小姐身在小舟之上 可能还有危险 不如拿着伞回去吧 也怕家人担心 这一回小姐看了看漫天水雾的湖面 有些动摇了 那实在有些 习水见小姐还要客气 直接走上前去 把怀里还带着体温的纸伞递了过去 海王小姐不要推脱 衣衫打湿了不打紧 就怕寒气入体 染上了风寒 不易调养 那 那好吧 湖面本就湿气大 更逢阴雨天气 这一身细纹罗纱早已浸湿小半 贴在身上极为不适 见小姐已然伸出纤纤玉指接过纸伞 此情此景 溪水犹如听见心里一朵花开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成百上千的中年男正像看电影一般 死死盯着一幅长达百米画卷里情景 这幅画卷粗看之下像是一幅成郭的血实 可细细看去 却处处透着诡异 明明是晴朗的天空 却下着暴雨 明明是含苞待放的鲜花 其根已经枯萎 明明是天真浪漫的孩童 却有着死尸一样的僵硬 明明是接亲的花轿 里边却坐着烟花巷子里的头牌 画面正中有个小人端端坐在一处吊着死鬼的菩提树下 不声不色 不动不摇 不语不笑 就像一个泥菩萨般没有一点反应 再仔细看去 那眉眼分明就是习水 此刻完全像身在室外一般 画里所有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一个推着自己骨肉去卖的农夫 推着独轮车一头撞了上去 溪水依旧如我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群蝴蝶 啃食着倒在地上的躯体 仍闭眼入定 天空落下一道彩虹 劈的皮开肉绽 也依然没有一丝反应 中年男开始坐不住了 试着用各种方法 只要能让这画里的主角睁开眼 哪怕是动一动 仿佛都变成了世上最难的难题 他怎么了 死了吗 怎么会呀 不可能 他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动作 他在装见鬼 为什么试了这么多手段 还不见他醒过来 如此下去 心血岂不是全部白费了 快把他换回来 你们谁还有办法 只要能让他手指动一动就行 中年男们炸了锅 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折磨人的手法通通用了上去 就见画里的习水如同一个血肉木偶一样 受尽各种非人的痛苦 这一刻被鞭打的皮开肉绽 下一刻放空了鲜血 刚受尽了炮烙 又马上五马分尸 被刀剑腰斩 紧接着撒满了密密的海盐 所有的酷刑没有产生一丁点作用 就像落进湖面的细雨 溪水依旧还是最初的模样 哪怕在这幅画卷里已经死了一千次一万次 中年男 或者叫画师更为恰当一些 到最后终于计无可失 成百上千个纸片人发出不甘心的怒吼 咆哮声响彻整个黑白天地 甚至从远处还未化完的山峰传来回音 更衬托出意想不到的失败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画师想到唯一一种可能 才可以解释眼前少年丝毫不为所动的答案 那就是他已经遁入自己所创造的幻境中 再不为外界所有的一切所能打扰 怎么会 他才十六岁 只用了区区三天时间 这 这简直不敢想象 在想到答案的那一刻 画师面前的画卷开始模糊 所有纸上的事物一样一样的画成一团团墨迹 直到所有的墨迹连成一片 除了画面正中依旧忘我的席水 不知过去了多久时间 也许是一刻钟 也许是一整天 也许是许久许久 溪水终于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不再是像前几次那样像镜子般破碎 而是像在抹匀的调色板被大雨冲刷一样 洗去浮色 只留下最本源的色彩如同洗尽铅华般返璞归真 不再有光怪陆离的虚幻 待周围的景物彻底稳定下来 溪水环视四周 发现自己半靠在一张沙发里 周围的家具如此眼熟 只看一眼马上就想了起来 这里不是其他地方 而是十六小子的山顶小屋 只不过和上一次来相比 此刻灯火通明 面前还是一桌子棋牌 餐桌上的剩菜剩饭已经撤了下去 带管家功能的小机器人正监督着扫地机器人作业 空气里有股好闻的气味 像是厨房正炖着一锅白粥 客厅里或站或坐着几个人 洗水挨个看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