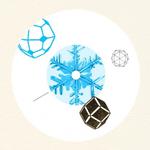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传习录 徐爱录第九集 徐爱轻声问道 先生 学生想请教您关于文中子和韩推之韩愈的见解 先生手抚长须 不紧不慢的说道 韩愈不过是文人当中较为出众的一位而已 而文中子 那可是一位贤能的儒者 只是后世之人往往只因文章词句写的精妙 便大力推崇韩愈 殊不知韩愈相较于文中子 实在是相差甚远了 徐艾有些疑惑的追问 先生 那文中子既然被您如此称赞 为何他又会有模拟经书这样的过失呢 先生微微一笑 耐心的解释道 这模拟经书之事 可不能一概而论d加以否定 你且先说说看 后世的儒者们著书立说 他们的意图和模拟经书相比 又有何不同呢 徐爱沉思片刻 然后认真的回答 学生以为 世间儒者著述 虽说不能排除有追求声明的念头 但他们大多还是期望能够借此阐明道理 而模拟经书 看起来纯粹只是为了博取名声罢了 徐生轻轻点头 接着又问道 那这些儒者著述以阐明道理 他们又是效仿何人呢 先生毫不犹豫的回答 自然是效仿孔子删改编书六经以阐明道理之句 先生反问道 如此说来 那模拟经书难道就不是在效仿孔子吗 徐艾说 著述能够对道理有所阐发 说明模拟经书似乎只是模仿表面形式 恐怕对阐明道理没有什么帮助 钱生说 你认为阐明道理是要让人们回归质朴醇厚 并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呢 还是只是用华丽的言辞来粉饰 以欺世盗民呢 天下大乱 是因为空洞的文辞泛滥 而实际行动衰微 如果道理能在天下昭明 那么六经就不必去编述了 孔子山改编书六经 是出于无奈之举 从伏羲画卦开始 到文王 周公时期 其间论述易经的像连山 归藏之类 形形色色不计其数 一到变得极为混乱 孔子看到天下喜好文辞的风气日益兴盛 知道这些学说家没有止境 于是选取文王 周公的学说家一阐释 认为只有这些才抓住了根本 于是各种杂乱的学说都被废弃 天下论述易经的才开始统一 尚书 诗经 礼记 乐经 春秋都是如此 尚书从点谋之后是经 从周南 朝南以下 像九丘 巴索等所有那些淫民 浮夸的词句 大概有成千上百篇 礼气 月经中的民物 制度等 到这时也多得数不清 孔子都进行山削整理 使之正确 然后那些错误的说法才被废止 比如在尚书 诗经 礼记 阅经中 孔子何曾添加一句话 如今的礼记 各种解说 都是后世儒者牵强附会而成 已经不是孔子原本的样子了 至于春秋 虽然说是孔子创作的 其实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 所谓笔 就是记录那些史实 所谓学 就是删减那些繁杂的内容 只有简 没有增 孔子编书六经 是担心繁杂的文词扰乱天下 只是想精简却做不到 他是要让天下人务必去除虚文而追求实际 不是用虚文来教化 春秋之后 繁杂的文词更加兴盛 天下更加混乱 秦始皇焚书而获罪 是出于他的私心 而且不应该焚烧六经 如果当时他志在阐明道理 把那些违背经典 背拟常理的学说都拿来焚烧 那也正好暗合孔子删术的本意 从秦汉以来 文辞又日益兴盛 如果想要全部去除 肯定做不到 只应该效仿孔子 选取那些接近正确的加以表彰 那么那些怪异荒谬的学说 也应该会渐渐自行废止 不知道文中子当时模拟经书的意图是什么 我神切的认为 他做的事有可取之处 我认为即使圣人再次出现 也不会改变这种做法 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 只是因为文辞兴盛而使其衰位 人们各抒己见 追求新奇 以相互标榜 用来迷惑世人 获取声誉 只是扰乱了天下人的心智 蒙蔽了天下人的耳目 让天下人纷纷争着修饰文词 以求在世上出名 而不再知道有注重根本 崇尚实际 获归治朴醇厚的行为 这都是著述所引发的 传西录徐爱录第十集 徐爱问先生 学生以为著述已有其不可或缺之处 就拿春秋来说 若没有左传辅助解读 恐怕众人难以透彻理解其中深意 先生微微摇头 说道 若春秋非得依靠船才能明晰 那岂不成了如歇后语般的谜语 圣人又何苦创作如此奸神野会之此 且左传多为鲁史旧闻 若春秋必须借助它才能让人明白 那孔子当初何必对鲁史进行山修整理 徐艾沉思片刻 接着说道 伊川先生曾言 传是案 经是断 例如经文中记载弑君法国之事 如不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 恐怕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先生耐心的解释 伊川此说 孔是研袭世间儒者之论 并未真正领悟圣人作精之深意 你看经中记载世君 世君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大罪 何须再追问其详细过程 征伐之事 应由天子主刀 书中既伐国 伐国即为有罪 何必探究其详情 圣人编书流经 志在端正人心 存天理 去人欲 对于存天理 去人欲之事 圣人会依据众人请教 依不同情况分别阐述 但也不会多言 只因怕众人仅专注于言语表面 故而有语无言之感慨 若为助长人欲 泯灭天理之事 圣人怎会详加叙述 那岂不是助长祸乱 诱导奸邪 正如孟子所言 仲尼之门无道还门之事者 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乃孔门之家法 而世间儒者只专注于称霸者的学问 万是功利之心 与圣人作精本意背道而驰 如何能想通其中道理 言罢 先生不禁感叹 若不是心怀天德 悟性极高之人 时难与之谈论此等要义 先生又道 孔子曾言 吾有及使之却文也 孟子一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 吾与五成取而三策而已 孔子山书庞于下司 五百年间仅留数篇 难道此期间无其他诸事 禅所记仅此 圣人之意以昭然若揭 圣人志在山凡 就见后世儒者却已味增添虚 爱疑惑的问 圣人做精意在去人欲 存天理 如五霸以下之事 圣人不欲详述 此里学生已名 但尧舜以迁之事 为何简略之 鲜有所见 先生缓缓说道 无惜皇帝之事太过久远 诸事流传甚少 此情形不难想象 彼时全然是醇厚质朴之风貌 毫无后世之文采修士 此乃太古之志 远非后世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