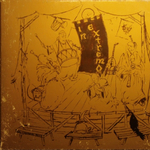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军医长来到
诊完脉
一副药吃了下去
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
当时那兵断了气
大家都不知道
只听见他吃下药去
直嚷肚子疼
以后就再没有作声
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
等到出早操的时候
协同跑来查营房
大家急忙整顿内务
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
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
走进去一看
原来早已没气了
当时气得冯玉祥急忙去找军医长
他军医长是协统的儿女亲家
外号叫催命鬼
冯玉祥问他
好好的一个兵
不过生了点小病
你一服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
你这是怎么治的
你这算什么医生
催命鬼听完质问后
军医长竟这样回答
吵是治病
可治不了命
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冯玉祥就说是
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
哼
那时军队中佣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
学识能力往往不大
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愤不平
也只好闷在肚子里
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
位置很高
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
他不知怎么犯的神经病
忽然上了个奏折
大意是行武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
台长以上的官长需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
消息传到各处
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
冯玉祥对于这件事情
当时发生两种感想
第一
其实军官学校太少
而且开办不久
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
以毕业人数论
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
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
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摇动军心
不能不算是师政
第二
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
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
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
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
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
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
这类哲虽然没有立即施行
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
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
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
也就是一九零五年前后
在河间彭德举行秋操
以示威吓
我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
北军是第三阵全阵
第六阵一混成邪
南军第四阵
全阵
第五阵一混成邪
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阵一混成邪从南院出发
分成两混成团
沿途自己欲行成习
因为参谋人员又只疏忽
指挥错乱
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
队伍看不见队伍
结果只有侧位同侧卫碰着
大队完全错过
后来一个左转弯
两军调过了方位
南军变成了北军
北军变成了南军
才开始打起来
段统治见状大为不易
立时吹紧急集合号
对官长指摘错误
大家申斥
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
等到第二次演蔽
已经七八点钟
当时来不及
蒋评即下令往松林殿宿营
那时天色完全漆黑
沿途人马杂踏
凌乱不堪
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
前后车辆拥塞
一发遭成一团
大官不耐烦
早骑着马先跑了
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
又都是新来的
也就不负责任
士兵们没办法
就胡乱落队
等到了宿营地
已是午夜十二点
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
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
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
哪知夜间下起雨来
越下越大哪照鹿血桶的意思
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
免得官兵衣服淋湿
到时不便演习
跑到段统治那里请示
段统治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
说怕淋湿衣服
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
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
并不是真的打仗
若是真的打仗
自然不用说了
协筒就碰了这一个钉子
当时生气
挂了病号
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
段统治仍然下令出发
那时雨越发大了
倾盆的下降
无法行走
段统治不知怎么异想天开
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
令炮队开炮
向天空轰一阵
说上面的后云受了震动
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
命令下来
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
当时声震天地
民众皆惊
不知到底什么事
打了半天
哪知雨不但止不住
反而越下越大
段统志非常气恼
拿出他的硬皮起来
说下不下都得走
立刻下令出发
当时现买草料
现买给养

![[冯玉祥]16参加新军的训练 2-文本歌词](/skin/ecms309/images/lazy.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