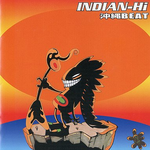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父亲当前就骑着日嘎出发了
他开始说服牧人出售牲畜的这天
雪哗哗下着
雪朵大的出奇
就像无数白蝴蝶在风中滑翔
碰撞
争艳斗起
忽而又变了
深阔的天幕变成了一架偌大的织机
不停的摆动着
把羊毛一样的雪花瞬间影成了线
又瞬间织成了铺路
这是多大一块洁白的上等铺路
任凭父亲肆意裁剪
然后缝制成世间需要的一切
辽阔无际的草原支着白铺路
铺着白铺路的草原可以沿着铺路的经纬线走向远方的草原
正在寒风里歌唱
父亲和日嘎被裹挟在铺路里
就像铺路的一部分
横一下竖一下
突然不动了
一顶帐房出现了
一声藏獒的闷叫出现了
一抹几处门帘的酥油灯的光亮出现了
父亲在帐房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主人扔了出来
一男一女两个牧人抬着父亲把他从帐房里扔了出来
父亲在雪地上滚了一下
就要爬起来
牧人的藏獒扑过来摁住了他
不远处的日嘎大吃一惊
长嘶一声跳了过去
转身的同时廖撅子就踢
藏獒后退了几步
轰轰的叫着
父亲懊丧的坐在鸡穴里
不明白自己的哪句话激怒了对方
竟至于让天性好客的牧人把他扔出了帐房
日嘎守在藏獒和父亲之间
也有些不明白
眼睛扑闪扑闪的
怎么了 主人
你不是一向都会受到牧人的欢迎吗
这家的藏獒也不明白
闻着看着是个好人
怎么会偷东西呢
在他的认知习惯里
只有偷东西的人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父亲站起来
慢腾腾往前走
身子沉沉的
腿在雪地上陷得很深
忽一下歪倒了
怕日嘎担忧
回头看了一下
赶紧爬起来
父亲走了很长时间才骑上日嘎
雪的飞翔正在加速
风急了
带着洪亮的嘶吼
原野上的奇影很快变成了雪人雪马
变成了属于荒雪自己的一景一物
行走显得更加孤独和凄凉
也更加吃力和缓慢
每迈出一步
都意味着陷入
松软的厚雪和强劲的风都成了大自然的毒挡
即使像日嘎这样矫健的马
也不能自由行走了
而远处的狼嚎
就像雪山大地送来的问候
温暖着父亲孤寒的心
在这寂静而苍茫的雪原上
毕竟行动的并不只是他和日嘎
毕竟狼不会抛弃他
相反
他们肯定会千方百计接近它
那就来吧
吃我
还是听我说
或者先听我说
再吃我
我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因为我只能那样说
那是实话
真话
非说不可的话
日嘎啦
你这是要去哪里
回县城
还是回爵霸家
还是回我们自己的草场
怎么离狼嚎越来越近了呢
不是一只狼
是十几只狼
我们会完蛋的
哈哈
日嘎
总有一天
你会带我走向死亡
但不是今天
今天我还要说
说那些实话
真话
非说不可的话
听 听我的话
离开狼群
去木家
去木家
父亲在心里狂叫着
只听呼啦一声响
大风撕开了遮天蔽日的雪幕
牛奶河一样的地平线咕咕而来
一顶帐房清晰可见
好啊 日嘎
原来你一如既往的知道我
知道我即使一千次被扔出帐房
也还是要去面对牧人的冷脸
那些雪缘一样没有色彩的冷脸
父亲看到狼嚎和帐房离得不远
中间隔着牛群和羊群
海海漫漫一大片
两个牧人和一只藏獒根本顾不过来
只能把住一端
让出另一端
似乎是说
那就吃吧
狼 狼 狼
吃饱了赶紧走
父亲和日嘎跑过去帮忙
好不容易赶走了狼
留下来说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天正在黑下去
大概是看在了帮忙驱赶狼群的面子上
这一家没有把父亲扔出去
但拒绝用饭时招待他
只让他喝完了说话之前端给他的那碗酥油茶
主人做出请的手势
说
我家的帐房实在是太狭窄了
请倒卖牛羊的人去找更宽敞的帐房过夜吧
父亲搭着日嘎来到不远处挖雪窝子
睡觉的时候说
日嘎啦
我拖累你了
害得你连口赞粑都吃不上
这么大的雪
到哪里去吃草啊
日嘎呼哧呼哧当大鼻孔向着四野闻了闻
扑噜噜打了个响鼻
像是在安慰主人
父亲丢开他
打着哈欠钻进了雪窝子
一闭眼就睡着了
他梦见日嘎流浪在雪原上
找不到草吃
扑通倒下就死了
他哭醒了自己
爬出雪窝子一看
天已经放亮
日嘎正在一群牛的中间
几头牛不断把反锄后本该再咽下去的食物吐到地上
日嘎伸长舌头
一点一点把热腾腾的食物卷到自己嘴里
父亲惊呆了
原来动物之间还能如此
日嘎肯定是这样表达的
我饿了
走不动了
但我还得带着主人走下去
请给点吃的吧
牛们肯定说
请原谅
大冬天我们吃进去的也不多
只能每个吐一点点给你
就是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言
肢体的
神情的
还是声音的
日嘎的肚子圆溜溜的
一百多头牦牛
一头秃一点那也是不老少的一堆食物
这一天
父亲和日嘎又访问了五户木家
结果都一样
拒绝买卖
拒绝他的说服纠缠
而且都不那么客气
信多贸易是什么
没听说过呗
你不会是骗子吧
都说做买卖的人是骗子
你说什么
把我们的牛羊给你
你拿去卖钱
凭什么呢
别说你不是公家人
就是公家人说了也不顶用
承包了牛羊和草场都归自己了
你卖了钱再把钱给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
你图个什么
再说
你要是躲起来不见面
我们去哪里找你
你说也可以先给钱再把牛羊拿走
那也不行
我们要钱干什么
能剪下羊毛来还是能挤出牛奶来
等他告诉对方自己也是一个牧人后
人家又有了别的想法
你是不是看着我们羊多牛朵心里不好受
你怎么不卖掉你自己的
什么
已经全部卖掉了
胡说八道
我不信
别向雪山大帝发誓了
全部卖掉的话
你就是个不安分的牧人
就是盗马贼一样的坏蛋
草原上容不下你这种人
走吧
我们忙得很
没时间坐下来跟你流水一样长长的说话
态度好一点的会招待他一碗酥油茶
但蘸粑和肉食就别想了
似乎牛羊越多
牧人越小气
似乎他真的是一个可怜的骗子
在被牧人一眼识破的尴尬中罗里啰嗦狡辩着
天黑后
父亲和日嘎来到了第六家账房前
父亲滑头起来
先不说来意
讨要了些酥油蘸粑垫了垫日嘎的肚子
钻进帐房吃了喝了
在人家的毡铺上睡到第二天早晨
又添了一碗折麻
才说起自己是来收购牛羊的
主人瞪起眼睛看着他
似乎意识到竟然让一个盗马贼一样的人留宿了一夜
招呼儿子过来
放倒父亲
抬起来
又一次扔出了帐房
父亲蹊跷的挑眉毛
瞪眼睛
牧人守旧
不知道钱的意义
把牲畜当做唯一的财富
不肯出售牛羊
这也在意料之中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怎么会变得如此野蛮
不仅不招待吃喝
还会动不动把它扔出账房呢
太过分了吧
他爬起来
冲着帐房门口的主人喊道
我是乡萨主任的朋友
你这样对待我
就不害怕我去阿尼琼贡告你的状吗
主人蹲下身子
抱着自家的藏獒
不让他扑向父亲
哼了一声说
我们见了乡萨主任磕响头
咚咚咚的磕九下
见了肩在曼巴也磕响头
咚咚咚的响九下
都是平起平坐的高人
你要是告我
我也会告你
肩在曼巴的法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父亲愣了
他听说过奸赞曼巴
是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游芳藏衣
哪里有不好
就会出现在哪里
一定是他给牧人说了什么
父亲说
奸战曼巴我不认识吧
要是你让我相信他的法力比香萨主任高明
我就不再到你家来了
主人惊慌的说
你还想来啊
我告诉你吧
曼巴说了
钱是世界上最大的魔鬼
会夺走牧人的灵魂
现在魔鬼已经放出来了
已经开始往草原上到处乱跑了
最大的灾难就要降临草原
你们要小心一点
谁给你们提到钱
你们就把它抬起来
扔到帐房外面去
原来如此
之所以不请他出去
而是扔他出去
是把他看成一个带来灾难的魔鬼
扔掉他
就等于惩罚了魔鬼
也远离了灾难
父亲说
请告诉我
艰赞
曼巴在哪里
我去向他请教的
要脸主人说
虽说曼巴的家乡是我们白纯路草原
但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有时候正在放羊
一抬头就见他从云端里下来了
父亲又是一愣
你说什么
我来到了白泉路乡
怪不得没有人认识他
雪太大
迷路了
一口气走到了白泉路乡
而他还以为自己在沁多乡转悠呢
心说那就不找奸赞漫
罢了
还是回庆多草原继续他的说服和收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