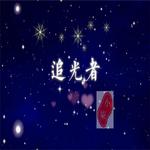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赵家遭抢之后
魏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
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
但四天之后
阿q在半夜里哭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那时恰是暗夜
一队兵
一队团丁
一队警察
五个侦探悄悄的到了魏庄
趁婚暗围住图古祠正对门
架好机关枪
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
把总焦集起来了
悬了二十千的赏
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
鱼猿进去
里应外合
一拥而入
将阿q抓出来
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
他才有些清醒了
到晋城已经是正午
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
转了五六个弯儿
便推进一间小屋里
他刚刚一踉跄
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儿合上了
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
仔细看时
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
却并不很苦闷
因为他那图古瓷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
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
渐渐和他勾搭起来了
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承租
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
他们问阿q
阿q爽利的答道
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
道德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的精光的老头子
阿q疑心他是和尚
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
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
也有满头剃的精光像这老头子的
也有将一尺来的长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
都是一脸横肉
怒目而视的看他
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
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
便跪了下去
站着说不要跪
长山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
但总觉得站不住
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
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
长山人物又鄙一试的说
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吧
免得吃苦
我早都知道了
招了可以放你
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
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吧
长山人物也大声说
呃
我本来要来投
阿q糊里糊涂的想了一通
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
为什么不来的呢
老头子和气的问
你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
此刻说也迟了
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嗯
他们没来叫我
他们自己搬走了
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哪里去了呢
说出来便放你了
老头子更和气了
哦 我不知道
他们没有来叫我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
阿q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
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唐的情形都照旧
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
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阿q一想没有话
便回答说
没有
于是一个长山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
要将笔塞在他手里
阿q这时很吃惊
几乎魂飞魄散了
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
这回是初刺
他正不知怎样拿
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叫他画花鸭
我
我不认得字
阿q一把抓住了笔
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儿
阿q要画圆圈了
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
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
阿q浮下去
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
他生怕被人笑话
立志要画的圆
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
并且不听话
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
却又向外一耸
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的不圆
那人却不计较
早已擒了纸笔去
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
倒也并不十分懊恼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
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
唯有圈儿而不圆
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
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
他想
孙子才画的很圆的圆圈呢
于是他睡着了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
他和把总怄了气了
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
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
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
拍案打凳的说道
成衣净百
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
抢案就是十几件
全部破案
我的面子在哪里
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
这是我管的
举人老爷囧极了
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
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
而拔总却道
请便吧
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
但幸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
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他到了大堂
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
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吗
阿q一想
没有话
便回答说
没有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儿
上面有些黑字
阿q很气苦
因为这很像是戴孝
而戴孝是晦气的
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复了
同时又被一职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
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
这车立刻走动了
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
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后面怎样阿q没有见
但他突然觉到了
这岂不是去杀头吗
他一急
两眼发黑
耳朵里惶的一声
似乎发昏了
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
有时虽然着急
有时却也泰然
他意思之间
似乎觉得
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
于是有些诧异了
怎么不向这法场走呢
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
在示众
但即使知道也一样
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
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他醒悟了
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
这一定是插的去杀头
他往往的向左右看
全跟着蚂蚁似的人
而在无意中
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马
很久违一
原来在城里做工了
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
竟没有唱几句戏
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
小孤霜上坟嵌堂皇
龙虎斗里悔不该也太乏
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吧
他同时想
手一扬
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
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
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
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住的前行
阿q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
午马似乎一一向并没有践踏
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
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
四年之前
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
永士不近不远的跟定他
要吃他的肉
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
幸而手里有一柄灼柴刀
才得仗这壮了胆
支持到魏庄
可是永远记得
那狼眼睛又凶又怯
闪闪的像两颗鬼火
似乎远远的来穿透它的皮肉
而这回
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
又钝又锋利
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
并且还要咀嚼他的皮肉以外的东西
勇士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器
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
他早就两眼发黑
耳朵里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
因为终于没有追赃
他全家都嚎啕了
其次是赵富非特秀才
因为上城去报官
北部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
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
所以全家也嚎啕了
从这一天以来
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已老的气味
至于舆论
在卫庄是无意义
自然都说阿q坏
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
不坏
又何惧被枪毙呢
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
他们多半不满足
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
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
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